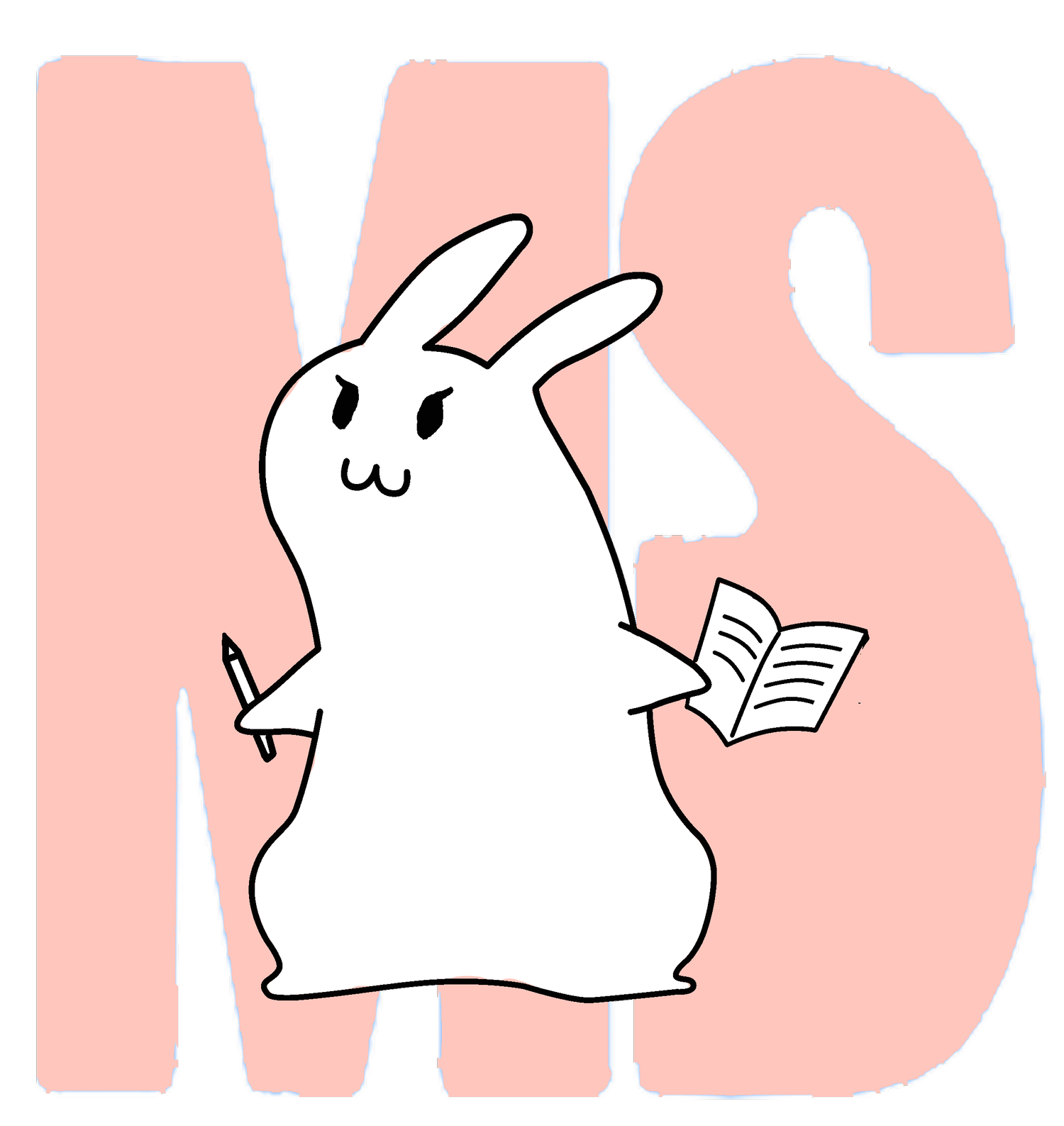还考不考虑留学呢?这让我想到了死亡那门课
我想起来时的路:靠在飞机的舷窗上,看一道道金光穿过波浪滔滔的云海,恍惚间仿佛来到《西游记》的开头,一猴一篙,远行求学,在夕阳下撑起竹筏,在汪洋中漂流浮沉。如果可以的话,我想亲眼目睹海上的莫测风雨。虽然翻不成筋斗云,但人生漫漫,自是风景,山水迢迢,路在脚下。
没有约会和电影的,不是纽约
新鲜感像一包水蜜桃,一掐,淌下汁水来,再一挤,源源不断地流呀流。即便在最严寒的天气,萧索的风吹进骨头缝,人的脑袋里也热得发烫,嗡嗡叫,旋转着地暗天昏。约会和电影一样,都在做fever dream。
谁能过情关,情绪的情
这是偌大的一座城在乌云压顶,是乱流的人潮在冲撞支离破碎。活在汹涌的情绪里,日日如大禹治水:白天堵,晚上疏。但至少,我们还未丢掉感知的能力,不失拥抱这个世界的可能。
哥大新闻系教我不再“精神内耗”
求真求变到了极致,不免幻梦一戳就破,存在主义危机四伏。看通看透到了顶点,不免踌躇自身不定,难以心无芥蒂地大步向前。也许《邮报》正披挂着新闻业的“知行合一”:面对总统的强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哲学的深思,怀敬畏之心而止步。也许这便是内心与世界和解的道路:能深深植根于下里巴人,又时不常想起阳春白雪。
在哥大学新闻:和陌生人说话
一支笔、一个本,将我镶嵌在社会大蜂巢里的一小格。立在汹涌的人潮里,我是一个才半只脚入门,还未及菩提老祖打三下、得真传,摇摇晃晃的“见习记者”。担上名号,仿佛画皮,在面上抹几层防羞霜,在心头裹严实铁铠甲。我在沉重与轻快中转圜跳跃,最终带着一摞笔记坐在电脑前,试图用几百个字写清采访数个小时的故事。
在美国开学:社交新手村指北
美国人的社交永远热闹,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社交媒体上动不动百来个赞。但若细究起来,轻轻拨开酒红色天鹅绒的帷幕,在幽黑的后台点一盏明黄的灯——人不过是人,中国人是人,美国人也是。哪怕文化不同、观点各异,人总只对有限的朋友交心,总只能被陪伴人生的一程,总逃不开酒肉之欢、君子之交的分别。
人类物种多样性 欣赏指南
纽约是教科书般的大都会。她包里装着纷繁错乱的历史,大踏步往前走,甩开一头五颜六色、混乱纠结的长发。纽约是贪婪的模样,因为纠集了全世界的好东西,一样也不肯丢下。因此纽约是一幅拼贴画,没有“我”,永远存在于许许多多当中。
耶鲁开学:与焦虑共生
我想这就是走出焦虑的密码:不是日夜用功去打败,不用心灵鸡汤来和解,而是敞开怀抱接纳一种情绪体验,以此为触点与世界相知,汲取生命的养分和能量。我们和焦虑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融为一体。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当我们变得无形无声,便不怕打不败一团空气了。今天是好天气,我终于再次走进校园,阳光洒满静谧的心底。
在耶鲁谈恋爱这件小事
我的室友开始恋爱了。某天凌晨三点半,我踉踉跄跄从图书馆爬回来,开门居然撞进一室昏黄:室友和男友还在视频通话,喃喃细语直到天光大亮。我模模糊糊地醒来,捞起电脑翻身下床,忍不住仰望天花板,叹一声爱情的荷尔蒙真伟大:不困吗,不累吗,不写论文考期末吗?
耶鲁使我明白:优秀是一种可怖的平庸,选择是一个无力的诅咒
我还在想,既然人生只活几十年,我能不能跑离既定的轨道远一点?能不能勇敢一次,就做一个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的选择,不再优秀得虚妄,而是定义属于自己的那一种“好”,那种脚踏实地、特立独行、不像绵羊一样的好?我想选一只我自己喜欢的动物,就那样活着,好不好?
2022年5月,耶鲁连办两场毕业典礼
两场盛大的毕业典礼后,两年的时光像是被偷去了一样。我怀疑人为什么执着于仪式,想起一场场生日、婚礼、葬礼,感叹人是如此善于,又如此需要赋予意义。生命是一个过程,假如不浓墨重彩地点上一笔,时间便在一念之间呼啸而去了。我们手里仅剩下抻得无限长的回忆,滑溜溜的,抓也不住。也许我们需要亲朋好友见证这个时刻,在肆意挥洒的阳光里走上讲台,由校长轻轻地拨一下学士帽上的穗,再抬头时笑得张扬又谦卑。也许这算是毕业典礼的某种意义:一颗年轻的心在喜乐祥和中对未来释然,于生命的又一节点沐浴新生。
人文学科还有未来吗?我在咖啡馆里追问耶鲁教授
阳光普照,驱不走世间冷峻漠然的神态。是教授的三言两语,带来了属于午后的温情暖意。他是那样儒雅和蔼、平易近人,像是家里的老人坐在书斋里,抬手拂去尘封往事的灰尘,心中还保有孩子气的纯净,缓缓讲起生命的故事。
留学耶鲁第一件事,居然是换衣服?
假如你也厌倦了城市里千篇一律的浮夸空气,耶鲁校园绝对是个清新的世外桃源:没有张扬的logo,远离横行的老花,免疫流行与时尚。在校三年,我养成习惯,出门从不打扮,因为再土再潮也没有人会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