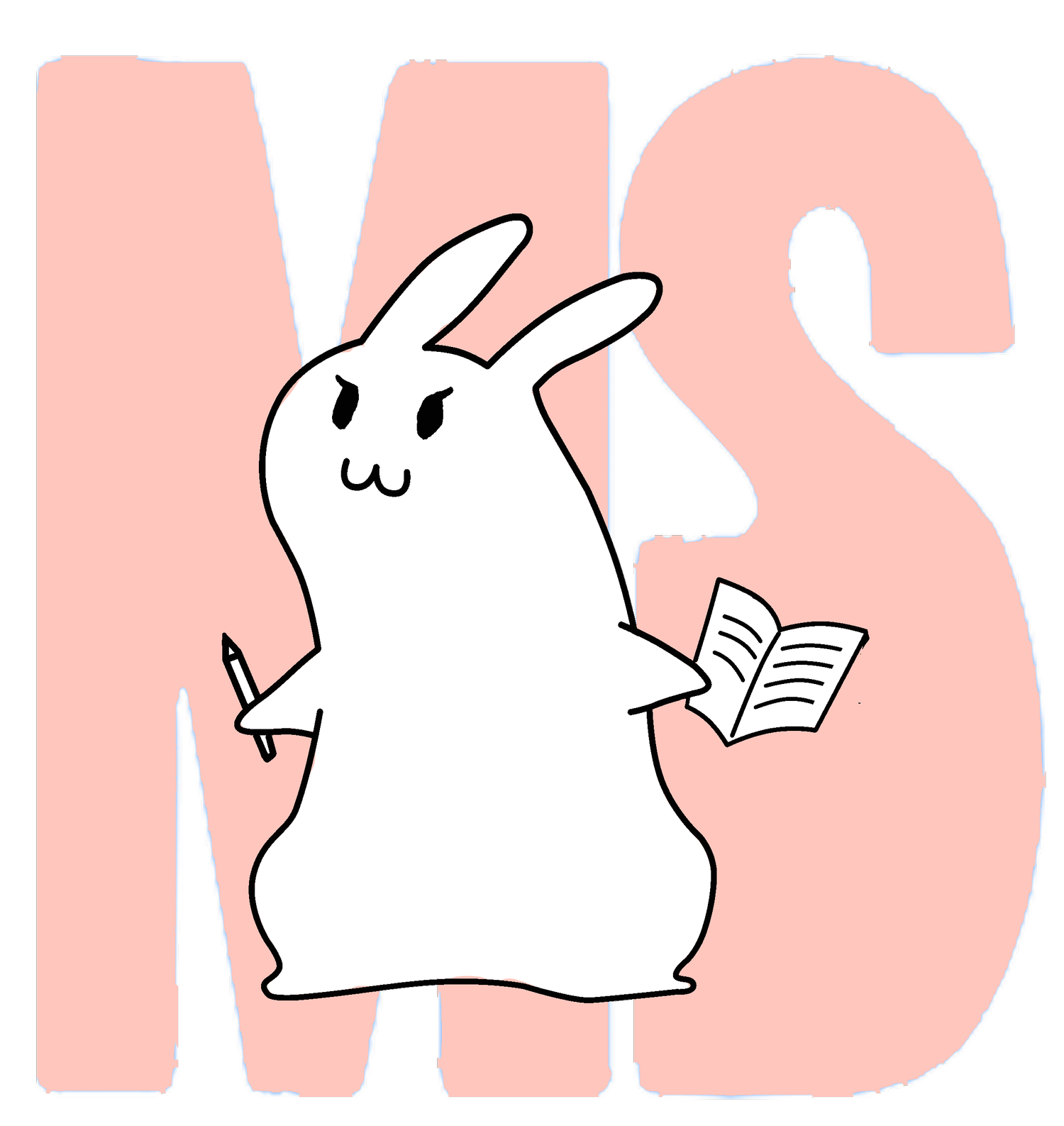在哥大学新闻:和陌生人说话
七月流火,纽约难得晴天。忙里偷闲歪在阳伞底下,向匆匆的路人行注目礼。“你会用ChatGPT写稿吗?”朋友问。我笑了,像在田野里奔跑的兔子。AI如鹰一般展开双翅,久久盘桓,高亢长啸。“不是不想用,是用不了,”我诚实答道。毕竟AI还困在电脑里,尚未化作人身,不像我们街溜子,窜行于城市街角,掏出纸笔就采访。
一支笔,一个本,在记者手里,就是大魔术师的黑礼帽,王牌特工的雨伞枪,是源源不息的流水和漂然的浮萍。哥大新闻系对我们采取“放养”模式:从开学第一节课起,就开始上街跑采访。我们必定要做好的一件事,恰恰是从小被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尝试的:和陌生人说话。
搭讪?只要脸皮在出门前涂厚一点,倒是不怕的。可新闻要变身故事,读来饶有趣味,光揪住路人聊天,加后期一通摘抄,实在是远远不够。为了找“对的人”,快速赢得信任,老师教我们的报道哲学是“transparency”——不要藏着掖着、半哄半骗,见面坦坦荡荡、开门见山:你好,我是记者,可以聊聊吗?
刚刚开学,我被分去报道大麻店。纽约的大麻虽已合法化两年,偌大一城的销售许可证才准发十几张。换句话说,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麻店,都算不上正规的销售渠道。抽合法,卖不合,但法不责众?管不了那么多了,四点钟下课去采访,第二天就要剪成片。我手里提溜一支大话筒,头上罩一副大耳机,肩上背一只黑不溜秋的设备包,抄起地图就往曼哈顿下城冲。
合法的店很少,也很富丽堂皇,在渐暗的绀青天色里,明亮得干净又温暖。被保安查了身份证进门,迎面撞见店中央一棵大树,周围环绕着香薰蜡烛、彩页画册,端的是设计师品牌的架子,摆出副当网红的志气。溜溜达达一圈下来,我发现大麻陈列在店尽头。深吸两口店里的精致气,又在心里擂鼓助威半天,终于朝柜台后的年轻女士开口:你对大麻售卖许可怎么看呢?
我一手支着话筒凑近,另一只手举起录音器调参数,边听边轻轻点头,再分出半个脑子来想下一个问题。聊开没几分钟,一个魁梧中年男人上来打断:你有收到公关部门的许可吗?没有吧,那你不能采访,收起来赶紧走。我见他自称老板,威风凛凛,店员也一改方才的嬉笑,噤若寒蝉起来,便礼貌道歉,安静离开。
许是这家店太贵,进出的客人不多。我站在街角,踌躇着采访不到消费者。一转眼,刚才的大叔正过马路——他走了,要不要再试一次?快要九点,录音器电量耗得真快。店门口的保安换了一人,我鼓起勇气,去征求同意。他很年轻,也很无奈,“我没法对媒体说话,但我支持你做的事,放你进去问问店员吧。”
前台的小哥长得斯文,像青涩时的演员“甜茶”。他对我的询问点头,却立即遭到了阻挠。三十多岁的白人女子一个箭步冲来:你要采访就出去。我一惊,呼吸凝滞,还是强装镇定,梗起脖子问:你谁啊?“我是经理。”她叉着腰,乍一看去像金毛狮王,言语间劲儿得骄傲。“好,我四处看看。”这总可以吧?她再次强调不许拿出话筒,才终肯离去。“真是抱歉,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这么凶,”小帅哥眨眨眼,悄悄说。我摇摇头,向他笑笑,步出店外。
夏末的风微凉,我直挺挺走了好远,眼泪才硬憋不住,啪嗒一声落下来。一个人用力擦脸,在心里给自己打气:老师说过,碰到对方态度强硬,并不是在针对个人,只是对记者的身份——证明你在人家眼里,是专业的新闻人了。我长叹口气,摸出手机,跳出好几通未接来电——原来是同学采访不顺,情绪崩溃。细细安慰几句,听她说好些了,便点开地图寻找下一家店。走走停停,在接受、拒绝里循环一整晚,到十一点,终于踏上了回家的地铁。
强撑着煮了碗泡面,狠狠挖了勺冰激凌,才想起这半天水米未进——怪不得好饿。似乎从未如此身心俱疲,又忍不住想,这一点点委屈,根本和太多人的苦难无法比拟。开学一个月来,我听过教堂的神父讲故事,看白发苍苍的建筑师说历史,采访步行千里过境的难民。许多人不敢和我们说话,凡能说的男女老少都红了眼眶,讲起许多人死在路途上的险恶丛林,湍急的河流冲起婴孩的尸体。而活着到纽约的人,尚不知明天在哪里。
一支笔、一个本,将我镶嵌在社会大蜂巢里的一小格。立在汹涌的人潮里,我是一个才半只脚入门,还未及菩提老祖打三下、得真传,摇摇晃晃的“见习记者”。担上名号,仿佛画皮,在面上抹几层防羞霜,在心头裹严实铁铠甲。我在沉重与轻快中转圜跳跃,最终带着一摞笔记坐在电脑前,试图用几百个字写清采访数个小时的故事。
和陌生人说话,好难,但有趣。这世间,难事总要有人做,只怕安逸久了日子无聊,好过AI扫荡真成终结者。也许人生必要曳着一丝怅惘,为深夜emo提供养料。也许我们深深扎根的生活,恰如李商隐的诗:路绕函关东复东,身骑征马逐惊蓬。天池辽阔谁相待?日日虚乘九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