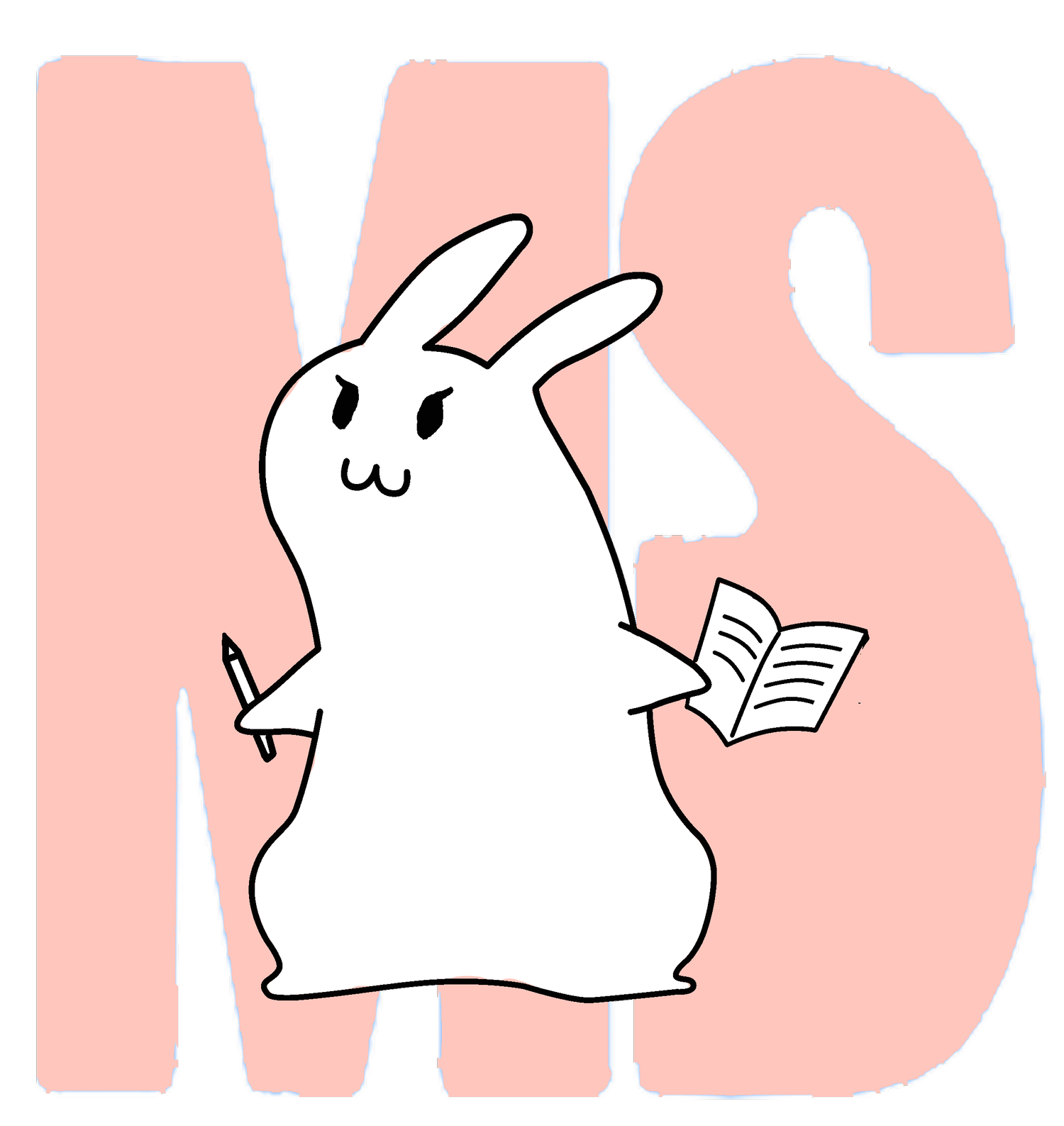外婆最后的礼物
外婆去世的那天晚上,是深秋。十二点多我们从医院回家,凌晨三点被电话吵醒。十六分钟后,
我在病房里见到刚刚咽气的外婆。
这算不算是见到了最后一面呢?不敢细究下去,只觉得心头的每一寸都凉得发僵。我身体的一切
都凝滞了,不会想,也忘了如何去感受。
静止的时光里,浮动着的每一点细节都如此鲜明。我好像在半空中朝下看自己:蓦地睁眼,怔怔
地下床,犹豫两秒要穿不要多件外套,然后以最快的速度走进车库。窗外掠过晦暗的夜,那是别
人好眠的梦境,是熄灭了的万家灯火。直到医院的白光将我唤醒:空气如凉水,我走进有死亡的
现实世界。
据护工阿姨说,外婆在生命最后的十几分钟里,一直在无意识地喊着 mie mie —— 她叹道,还是 想妈了。哦,我才明白过来,原来那是“妈”的声音,变了形。后来有一天,我从梦中惊醒,突然 意识到:是不是护工目睹过太多死亡的瞬间,所以听懂了我听不懂的话。这算不算是一种“懂 行”?
外婆从小当家,练就一身照顾人的本事。幼年丧母后,姐姐去上海读书,她的外婆又是地主家裹
小脚的小姐,她自己带妹妹长大,边上学边把家里的活全包了。后来,外公常年不着家,一夜一
夜地搓麻将。他喜欢玩,没什么责任心,也躲着外婆的急脾气。于是,她又是一个人拉扯一整个
家,带着年幼的舅舅去办公室。再然后,她提前退休来照看我,又回老家去带小表妹。
她一生要强,对太多人好,却也累了吧。我好想抱抱她。原来,人到最后又回到原点,会变回惶
恐无依的婴孩,唯一能够寄托的,不过是记忆深处母亲的影。
过世前的一周里,外婆的免疫系统彻底瘫痪了,只靠不断加大剂量的镇定剂,才勉强可以入眠。
我和妈妈一起站在深秋的风里,她说那相当于全身毒发,不知道有多痛苦。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个
夜晚,也是宁静的夜里,我和外婆躺在一张床上,聊不完的话。她和十一岁的我说,希望可以平
静地死去,最好是睡一觉,人就没了。
病痛如此残忍,一点体面也不留,和死亡交接班的时候,还要搅和掉最后一点念想。
外婆的脸凌乱,简直不成人样:面色青白,一只眼的睫毛掉了一大半,没有牙,嘴唇瘪着陷进
去。她才不要这样呢。她很喜欢喷香水的,夏天里的手绢、扇面都是香喷喷的。她用了一半的颈
部精华,还立在家里的洗手台上。她怎么能看起来这样不体面呢?
我想像原来一样亲吻她的面颊,却在一阵慌乱的心绪中退了一步。我轻轻地握住她的手。在她病
重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是这样握着她的手。一双那么巧的手,早已被插满了针眼,没有
温度。
母亲和护工合力,为外婆脱下病号服,擦拭全身。然后该穿寿衣了。另一个病房里的护工跑来,
嘬着腮,大声指点起经验来,硬要亲自上手。母亲安静地拦下了,亲自把一层层衣服套好,最后
戴上帽子。巨大的红色棉服把外婆淹没了,衬得她久病的身躯格外瘦小,压在沉重的包袱下,埋
在漫天的苦楚里。清高了一辈子的人,在最后的时刻,只好无奈地弱小下去。我在病房的角落里
站着,静静地看。最后,母亲拿了一叠钱给两个护工,那个不请自来的就喜不自胜地离开了。不
用亲自上手就赚到外快,今天对她来说是个好日子。
我模糊地意识到,这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了。我一厢情愿地认为这就是我爱的人,可什
么是人呢?人分不分灵魂和躯壳?我又跑过去想拉住她的手,却见其已经发青地肿胀起来了。
白色的灯照得一间屋子格外宁静,好像一场剧烈的痛苦从未发生过一样,好像外婆在病房里几个
月的时光,已经随着她的生命骤然消逝了。
随后,两个穿着黑衣的男人进来,外婆被搬上一张不锈钢的带轮子的床,被推出了病房。我们一 行人走进电梯 —— 下坠,无尽地下坠,在黑暗与绝望里。门开了,是一间暗淡的小屋子,一整面 墙上都是铁灰色的不锈钢柜子。一个格子前,发着红黄交错的光。我看不大清,被泪水模糊了眼 睛。
电梯里只剩下我和父亲。我蹲下,抱着膝盖号啕大哭,一只手拽着他的衣角。过了不知道多久,
他拉我站起来,目送着外婆的身体被推进柜子里的一格。黑衣男人拿起一张纸,为母亲介绍起供
奉蜡烛的价钱。我这才看清,原来房间里那一点异样的颜色,是一笔趁人之危的财富,是一缕无
所适从的哀思罢了。然后,黄色的火光烧起来,一点一点侵蚀红色的蜡。
走到门又,我又深深地望了一眼那一块格子,大脑麻木而清醒。原来这就是死亡,这就是归途。
原来没有知觉的身躯,会躺在恒温恒湿的柜子里,然后被涂脂抹粉地摆弄一番,再拉去葬礼。原
来殡葬业如此欣欣向荣,原来这就叫赚死人钱。原来整个世界混乱又无情,而我不过是在长辈的
爱与呵护下,成为了被上天眷顾着的,快乐地长大的那个人。原来死亡是无可抗拒的力量,是再
坚强的意志,再深厚的感情,再努力的挽回,都永远不能更改的定局。原来一切是空,原来一切
都没有了,原来唯一的依靠不过是残存的记忆。原来我要用那么多的时间,为童年的黑白录像
带,涂上鲜艳明亮的颜色。从此,外婆便是这许许多多的片段,是我与母亲谈话时的一段段故
事,是在梦里常常出镜却抓不住的亲人。
原来我再也见不到外婆了,再也不能和她说话了,一句都不能了。我一直哭,放不下。原来这就
是死亡。
在她还清醒着能说话的时候,曾经有好几次,拉着我的手问我男朋友对我好不好。我说很好,你
放心,我一切都很好。她拉着我的手,轻轻地说,那就好,一定要找一个能够好好照顾你的人。
后来我和男友分手的时候,脑海中总还是这一场画面。外婆辛苦了一辈子,对爱情与婚姻,只对
我留下一句发自肺腑的感慨。我知道她心疼我。不管是单身、恋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我总
记得这几句话。遑论对错,只因这是我唯一能牢牢抓住的东西。
白色的病房像一场孤单的梦,飘零在闪着彩色泡泡的青春里,像一叶扁舟在海浪里起伏左右,坚
韧地守护着我心里的整个世界。外婆留给我最后的礼物,是一场深切无依的痛苦,是比身边的同
龄人早一步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