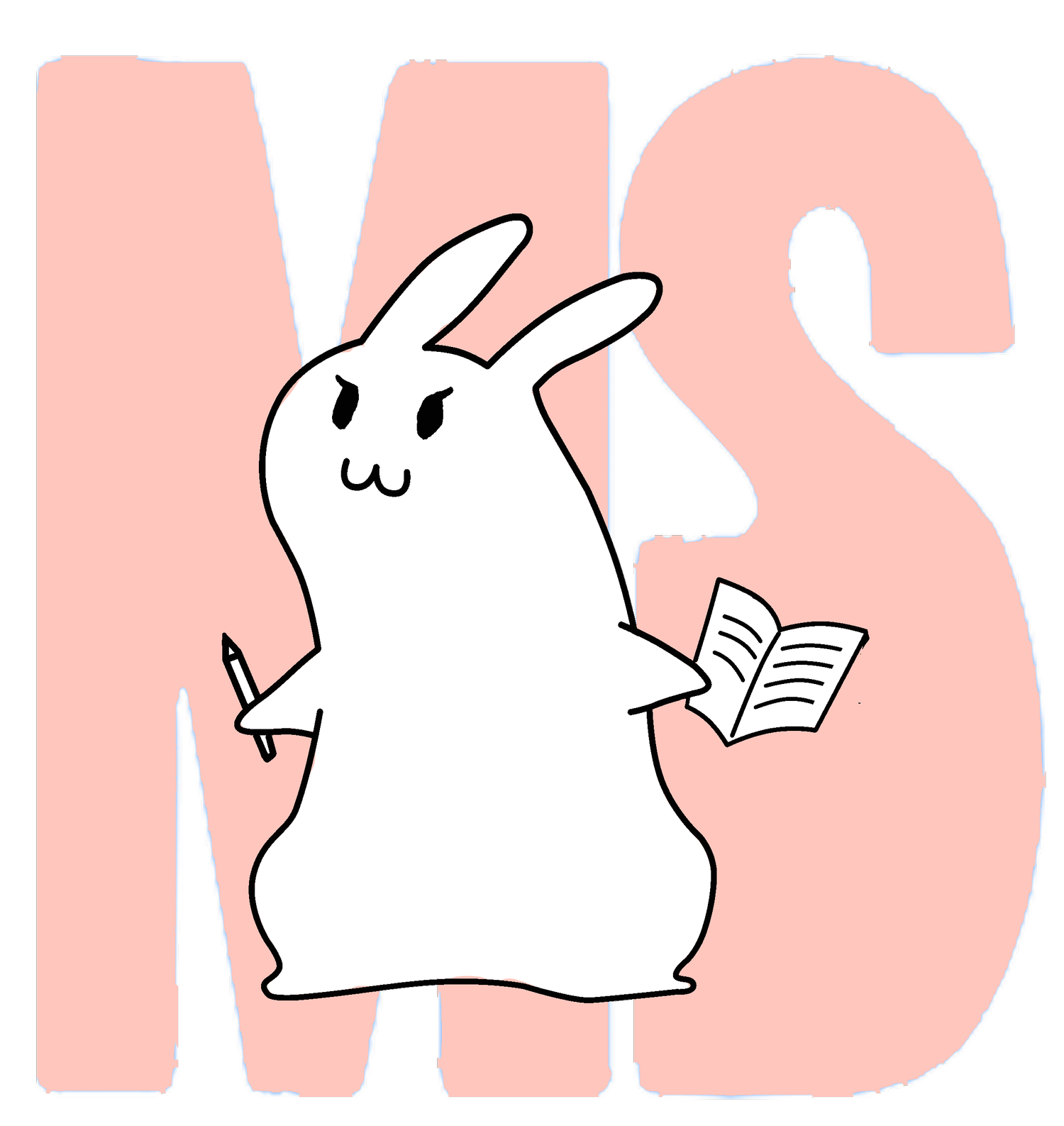耶鲁使我明白:优秀是一种可怖的平庸,选择是一个无力的诅咒
第一次暑假滞留在学校,本意是躲个清净,没想到夏日校园格外热闹,落了满地新奇的目光。上学的时候,街上熙熙攘攘,人人行色匆匆。宿舍、教室、食堂、图书馆、社团 —— 日历被涂得花花绿绿,每一个时刻都被用来奔赴下一个终点。暑假可不一样了,空气中漂浮的再不是来自熟悉的漠视。上夏校的高中生坐在傍晚的草地上,萤火虫忽明忽暗地扑闪,一阵阵翻涌,像阳光下海面的波浪。少男少女舔着冰激凌,谈人生聊理想讲八卦,风中拂过一阵惬意的憧憬。
我很好奇,他们眼里的耶鲁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智慧的殿堂,驰骋的草场,是不是即将供他们扬帆的海港?他们会不会满眼向往,一旦踏上这一片土地,大千世界正在眼前,光明的路从鲜花盛开的脚下,延伸到很远的天际。至少当年的我是这样,被一股新奇劲儿充盈得满满当当。大一开学,我去体育馆参加社团招新。从门口的高台往下看,人山人海,震耳欲聋,摩肩接踵,无处落脚。几百个社团挨在一起,桌子上支起海报,过道里横着吆喝。我深吸一口气,一头撞进了汹涌的人潮里。
如今回想起来,在当时一片眼花缭乱中,我心中的某根弦一定轻轻颤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隐约意识到,拥有很多选择这件事,是幸运也是烦恼,是礼物也是负担,是祝福也是诅咒。因为选择一多,就会忍不住什么都想要。这甚至不是主动的贪婪,而是下意识的路径依赖:因为曾经学习成绩优异、课外活动丰富、朋友多、睡觉少,便相信只要继续这样做,就可以成为名校的“天之骄子”。
于是,大一的我学会了一个词叫 FOMO = fear of missing out = 害怕错过。错过什么呢?任何事情。从一场聚会,到一句谈话,没有人舍得提前离场,没有人狠下心选择放弃。大一的我还学会了,在耶鲁夸人的最高境界是说他 work hard, play hard = 学得好,玩得也好。在图书馆学到凌晨的是他,在聚会上喝到昏厥的也是他,被万里挑一选进某知名社团的是他,找到大厂实习的也是他,走在街上和无数朋友热情打招呼的还是他,这样的他被视为一个很“酷”的人。
但是,这意味着他要同时做好多件事情啊 —— 真的能做好吗?我不知道。不过也许,只是也许,看上去酷,就只是看上去而已。大二的开始,我去听了一门法语入门课。零基础的我刚坐下正在发懵,对面一排人已经叽里呱啦讲得好流利。下了课一打听,发现人家高中已经上过四年法语了。另一次幻灭来自《耶鲁大学幸福课》,据统计是全校最受欢迎的课。可我听某位上过的同学诚恳告诫:别去,这课没我们想的那么好水GPA。哦,原来有一部分欢迎,是这么来的?好吧,人家就想拿个好分数,找个好工作,有什么错?哪有学生不找尽空子划两下水呢?但仅仅为了名次学习,而不是为学习本身,这似乎不是我憧憬里的耶鲁学子,至少不是我希望自己四年下来变成的样子。
我想这是选择太多带来的诅咒:学习、活动、社交、运动、睡觉,有太多可以做的事,美好得让人舍不得放弃,所以一桩一件都攥在手心里,却像一把金黄色的流沙漏出指缝。我看到一句话,完美地形容了这样的状态:问题在于,你参与的事情越多,你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最后什么事情都做得不理想。
这份精辟来自前耶鲁英文系教授德雷谢维奇,他在常青藤学习、教书多年后对美国名校的教育体制严肃批判,捧出一本《优秀的绵羊》。我对书名上这个努力、温顺、迷茫的形象深以为然。
我们这一群看似精英的学生,在无尽的选择中自乱阵脚,在既定的规则里激情斗舞。哪怕优秀,也如此寡淡,是不加气泡的白水,是甜得俗气的香草味,是人生的旅途被发了一张“好人卡”。这样的绵羊式的优秀,是一种无尽平庸的好,甚至不如某种轰轰烈烈的差。这还不是因为我们多年以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习惯了,在名校光环的荫蔽下舒服了,不敢往轨道外行差踏错一步,因此只想要沿着这一条路走到黑吗?我们无法有舍有得,是因为从小还算幸运,以为自己想要的都可以得到,便也没有意识到,人生的道路走到某一个交错口,是该学习做选择的时候了。
照书里说的,我们这一群耶鲁的学生,不过是“自命不凡的天之骄子”。我想,假使一个人不服气一辈子困在这个泡泡里,就该努力地跳脱出来吧。假使你不在里面,也该在此刻看清了这名校的招牌不过是阳光下七彩的泡沫,里面填了多少真才实学还得靠个人修养。我还在想,既然人生只活几十年,我能不能跑离既定的轨道远一点?能不能勇敢一次,就做一个和大多数同学不一样的选择,不再优秀得虚妄,而是定义属于自己的那一种“好”,那种脚踏实地、特立独行、不像绵羊一样的好?我想选一只我自己喜欢的动物,就那样活着,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