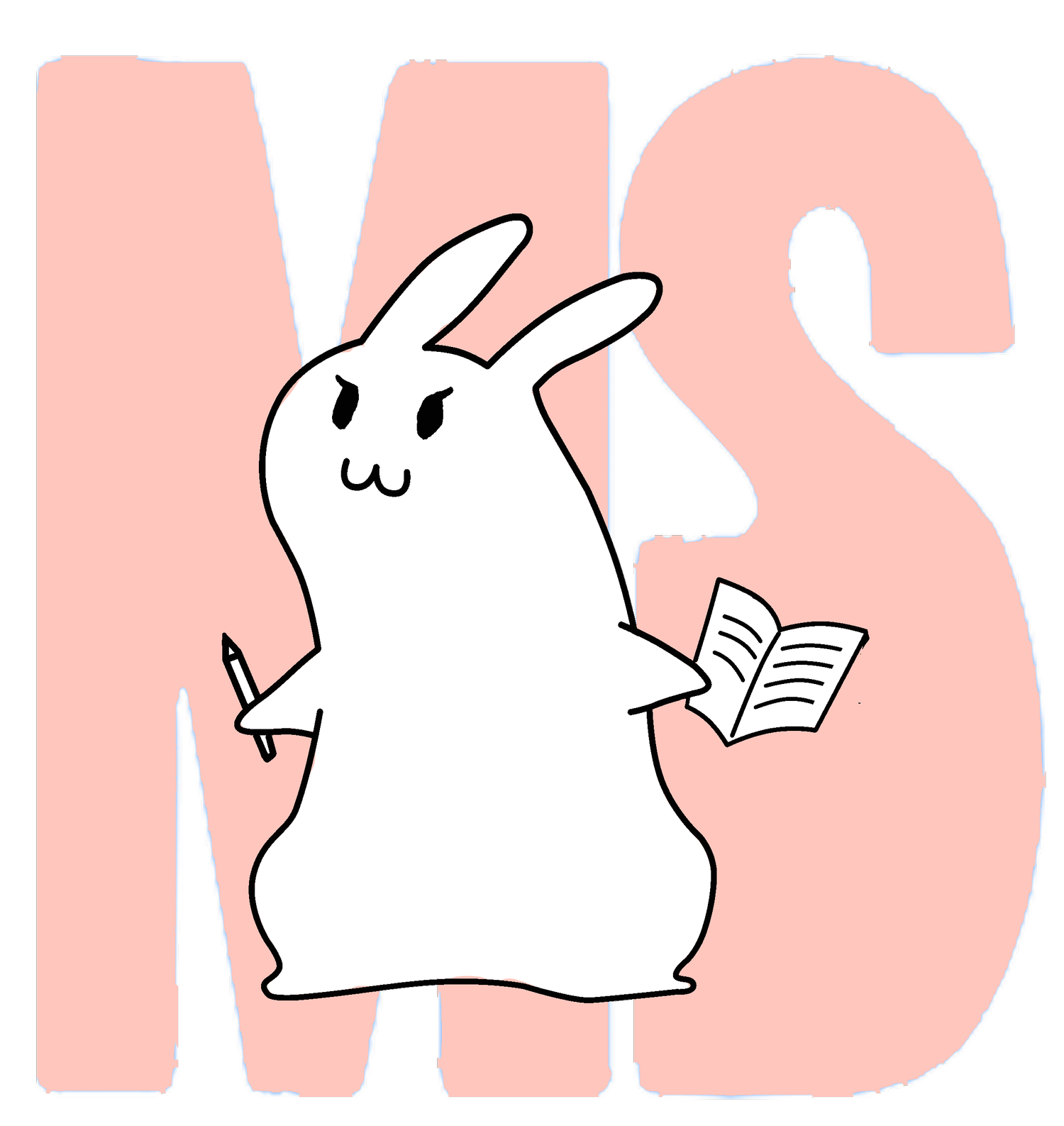人文学科还有未来吗?我在咖啡馆里追问耶鲁教授
早春的阳光像清水一样,缓缓淌过教授花白的头发。金色的光氤氲在空气里,那是一种浮于眼前的融融暖意。我手里捧一杯冒白汽的茶,踌躇地望向对面:教授穿一件寻常的羽绒马甲,正精神矍铄地啜一杯冷萃。
难得和教授一对一聊天,我攒的问题太多,直堵到嗓子眼儿,在我胸腔里擂起鼓来。眼看小半杯咖啡已经下去,我咬咬牙,还是从那个最核心,也最难回答的问题开始了:
“在当下这个被金钱席卷,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里,学习人文学科的意义在哪里?”
教授了然地笑笑,陷入短暂的沉思。我忍不住谈起困惑的来由:在注重效率的现代社会,文科的“没有用”仿佛成了一种原罪。没有科研的创新制造,没有大厂的上升阶梯,也没有金融的高薪风光。思想的世界如此深邃美妙,每每沉湎其中时却感到后脊背发凉,好像随时会被高速行驶的时代列车甩出窗外,落入贫瘠的荒野里。
搞了一辈子文学和艺术史,教授在耶鲁和斯坦福各执教十多年,如今已年逾古稀荣誉退休。他的语言有一种真挚的诱惑力,在一语道破玄机后使人豁然开朗,恍惚间已随他跃上一叶扁舟,徜徉在徐徐流淌的历史长河当中了。
几口咖啡过后,教授引述起法国作家罗兰·巴特的概念:读者的写作 (readerly writing) 刻意迎合大众的乐趣,作者的写作 (writerly writing) 审慎地追问自我与世界。
“总要有人去批判性地想,去无止境地问,”他说。
“哪怕作为这个社会里的少数派,哪怕大部分人永远无法理解,哪怕常常不被听见吗?”我问。
“对。”
他眨眨眼睛,湛蓝色的眸光温和又坚定。人文学者是冷静的观察者,从过去看到现在,挤过社会熙熙攘攘,穿越时代沧海桑田,幸运的话,还能瞥见一点未来。
我咬着纸杯沿,心头漫漫升腾起一股不可名状的不甘心来:没了?文科生就这样在劫难逃,注定要甘于寂寞,端坐冷板凳,过苦行僧一样的精神生活吗?原来未来已被束上枷锁:热爱的领域带不来优渥的生活,居然有点忠孝不能两全的遗憾。
我又感到惊讶:作为学界大拿的教授,此时难道不该振臂一呼,高举文明的大旗,说一些类似“没有人文精神人类就完蛋了”之类的警世恒言吗?他居然就这样平静地接受了现实,并将其缓缓铺陈开来,稳稳走在悲喜两极中间的那条钢索上。那举重若轻的姿态好像在说:看吧,此处没有光明大道,却有你认同的信念。选吧,孩子,这是你的一生。
教授以个人为根本的超然态度,是我从未预料到的陌生角度。在他的思想传统里,“学者”的身份意味着什么?故事从中世纪的修道院开始,教会在近千年前建起大学的雏形。那时学者和教权站在一起,对思想虔敬忠诚,与世俗泾渭分明,和政权分庭抗礼。时至今日,大学教授们依旧站在天平的另一端,摆出旗鼓相当的架势,作为旁观者审视当权者的言行。
与西方学者遥相呼应的,是我们的文人士大夫传统。“学而优则仕”,人生最得意事不过是从平民莽夫,一跃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分子。儒生的心中总画着朝堂的蓝图,怀着忧国忧民的抱负,肩上总挑着家国兴亡的担子,揽着兼济天下的责任。这样的理想,恐怕只有乘上一艘权力的巨轮才得见曙光。也因此,假如不再代圣人立言,我们的读书人眉宇间,免不了透出一点落寞的神气。
“可我们不一定是作壁上观的局外人,”教授见我只顾点头,补上一句。“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历史上,也许未见知识分子走上街头游行,但他们坚守自己的阵地:在后方教室的讲台上,结结实实改变了人的思想,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许,这是另一种“入世”之法。
阳光普照,驱不走世间冷峻漠然的神态。是教授的三言两语,带来了属于午后的温情暖意。他是那样儒雅和蔼、平易近人,像是家里的老人坐在书斋里,抬手拂去尘封往事的灰尘,心中还保有孩子气的纯净,缓缓讲起生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