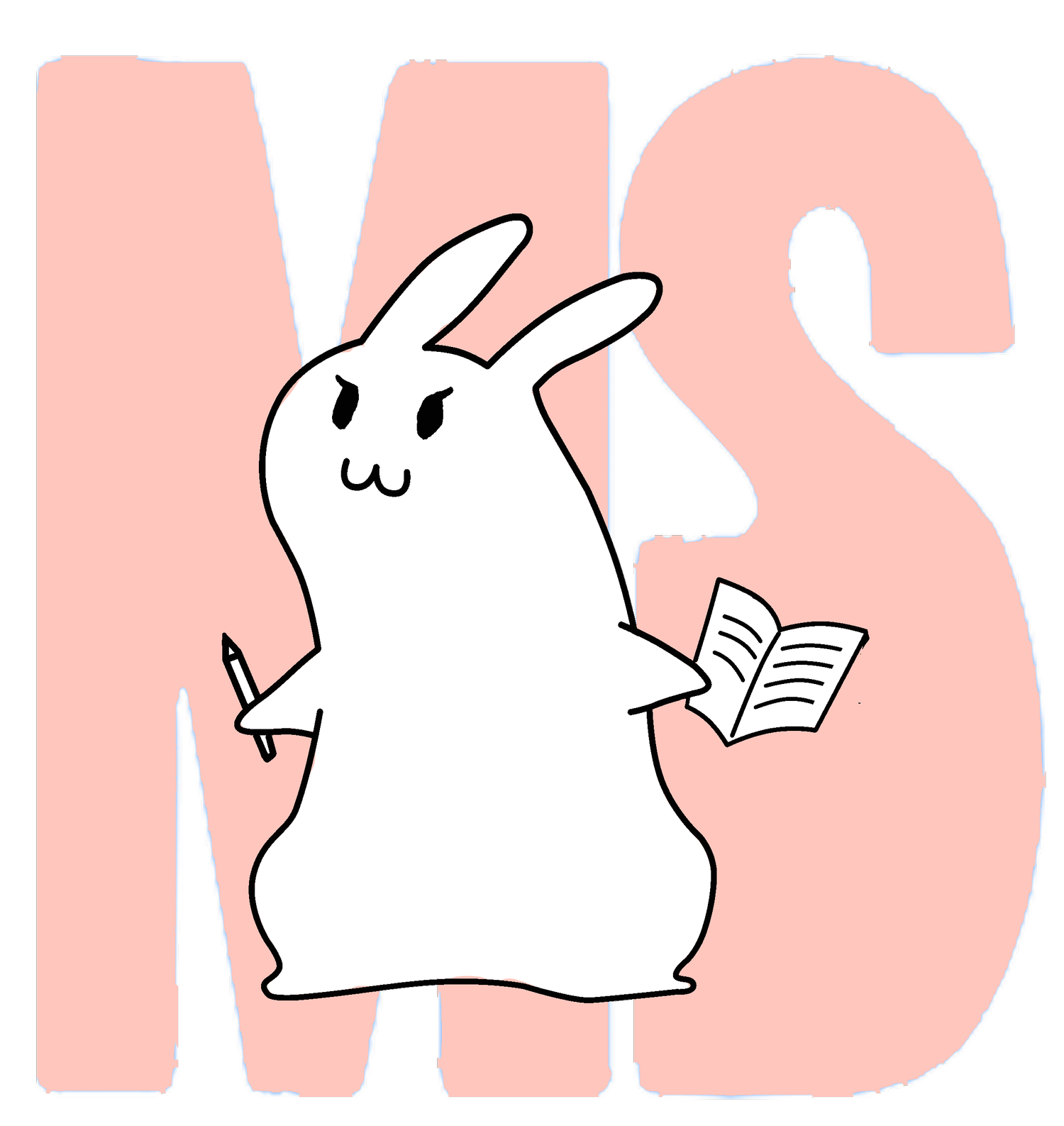哥大新闻系教我不再“精神内耗”
一个平常周二的晚上,纽约的秋风捎来凉意,撞上罕见晴天的余温。哥大新闻学院,《华盛顿邮报》的前主编来宣传新书——他叫马丁·巴伦,自从贝佐斯买下报纸后走马上任,期间带领团队数获普利策新闻奖,因报道被前总统特朗普电话轰炸,前年宣布退休写成此书。
我坐在人群边缘,翘着脚端起本子,边假装记笔记,边给他画小像:他长了一颗大鼻子,肉肉厚厚的,两片薄嘴唇,淹没在削短的花白胡须里。一副银丝边眼镜,架在高耸的颧骨上。简单的藏蓝西装里,一双腿瘦瘦长长。
作为新闻行业的掌权者,作为接触更上位者的常客,巴伦是美国左派精英的化身。他笃信新闻的力量,作为民主的保证。他当然对特朗普嗤之以鼻,笑言总统曾亲自电话半个小时,只因不满《邮报》的报道施压发泄,真是没有更重要事情可忙了吗?他没有,我可有。
确实自由——但对比台下的学生,甚至新闻院的老师,他又如一根橡皮筋,长长地向右派弹去。有人纠结于新闻“客观性”的辨论,他说在《邮报》根本没人提这茬儿。“说实话,我不在乎,”他笑道。作为概念,“客观”不是聊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又有人质疑报纸的paywall,即付费订阅模式,将许多人挡在信息的墙外。巴伦两手一摊,“如果没钱,连新闻机构都不会有,对民主是更大的伤害。”
在美国藤校待久了,似这般牢牢务实、不谈虚想的态度,简直是耳目一新。“观点太廉价,谁都可以有,”巴伦说,不屑于社交媒体上未经证实的大叫大嚷。“我从未见过哪位记者的推特改变世界,但我知道诚实、光荣的报道可以。”报道出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的《邮报》,历历壮举在新闻史上可谓是光辉熠熠。在巴伦看来,作为新闻记者,难的是踏实报道,难的是找到真相,难的是问好问题——那些未曾被解答的、甚至从未被提出的问题。
可问题是,何为求真?
上周为了报道,我来到刑事法庭的庭审现场。被告是一对黑人兄弟,不到三十岁,是曼岛贩卖可卡因的头目。引人入“黄赌毒”的歧途,理所当然是罪大恶极。但假如是正经营生,他们年纪轻轻、勤勉肯干,24-7服务客户从不休息,奋斗精神倒也值得尊敬。
后来和辩护律师聊天,听他吹牛赢过的官司,我越发肯定:即便法律的框架严格谨慎,在法庭中游走的却都是“人”。落入不同眼睛里的真相,碰撞起来,总酿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永无宁日。直到法官发话,陪审裁定,一锤落下,几家欢喜几家愁。
罗生门旋转不歇,但争辩总要落幕。真实有太多副面孔,求索到何处才是个头呢?
“真”是一场有限的追逐。作为新闻记者,自当志存高远,绝不能失了揭露真相的理想。可人总不能活在虚空的泡沫里,每日祈求太阳前来眷顾,才好散出五彩炫目的光芒。当然,人更不能永远附身屈居于淤泥之中,任由他人的苟且与肮脏糊住双眼。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生存,我们只好心如明镜,只好胸怀谦卑,只好奋力却不妄求。
也许这也是我们作为现代人,在东西方文化交锋中的生存密码。西方人总要求一个真,求那一位全知全能的神,那一套完美解释的体系。东方人总看到一个空,俯看人间种种皆为虚妄,仰望满天星斗却是无门。西方人总要求一个变,哪里的现状若看不惯了,必定上街运动抗议一番。东方人总看到一个通,在现存制度下辗转腾挪,最好不伤和气得其所愿。
求真求变到了极致,不免幻梦一戳就破,存在主义危机四伏。看通看透到了顶点,不免踌躇自身不定,难以心无芥蒂地大步向前。由此来到鲁迅的《拿来主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收并蓄地生活着、追求着。又如马丁·巴伦所言,辨论定义无用,践行实际才好。客观也好,真相也罢,好好报道、服务公众才是王道。
也许《邮报》正披挂着新闻业的“知行合一”:面对总统的强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哲学的深思,怀敬畏之心而止步。也许这便是内心与世界和解的道路:能深深植根于下里巴人,又时不常想起阳春白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