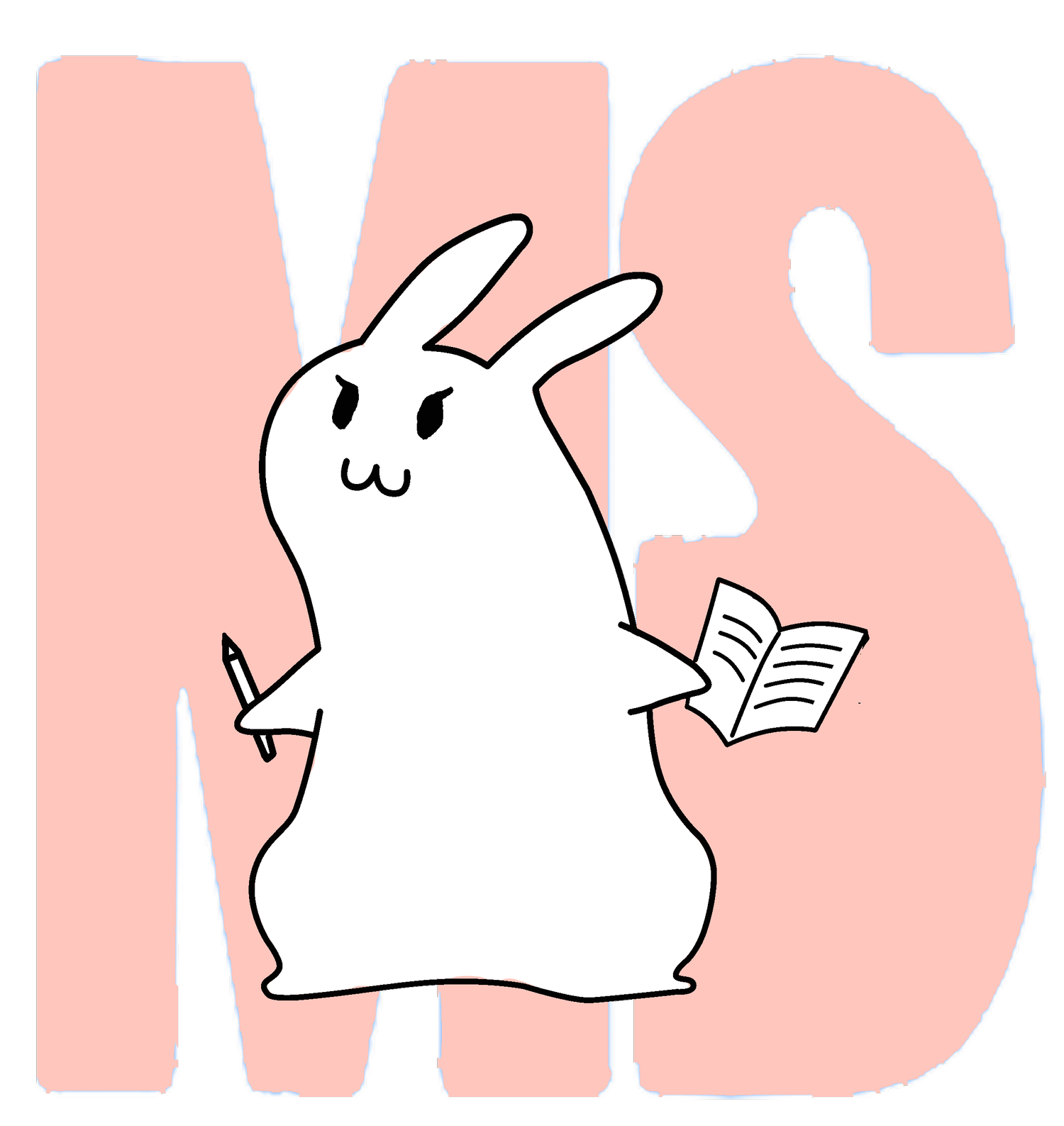2022年5月,耶鲁连办两场毕业典礼
最近一周,耶鲁连办了两场毕业典礼:先补上2020届迟到的仪式感,再复制粘贴一遍,按部就班为2022届毕业。五月的空气里流淌着温柔与狂欢,那是如饕餮般放肆的极乐,也是文雅而克制的骄傲。明媚的校园似已忘记攒了一冬天的阴郁,凄厉呼啸的寒风随着期末考的尾灯扬长而去。晚上八点了,天边还染着桃子一样的粉红色,娇俏地织进金色的霞光,隐入树影摇曳中高耸的尖塔。
随着毕业生家人的到来,本就生机焕发的校园愈发温馨动人。只要你披上一件学士袍走在街上,不知能收获多少猝不及防的善意。“毕业快乐!”街边舔着冰激凌的女孩对你歪头一笑,被微风吹起的鬈发在阳光下发亮。你腼腆地匆匆致谢,继续向前走,路遇一家久负盛名的冰激凌店 Arethusa。长长的队伍从小小的门脸伸出来,蜿蜒到街上。一家一家人散漫地等着,满是惬意安然。人都道耶鲁所在的纽黑文市以意式披萨闻名,可说起让学生们百吃不厌的美味,还要数这一家自营牧场、物美价廉的冰激凌店。只要区区五美元,就能端出满满两大勺,恨不能顶上一顿晚饭。你正犹豫要不要选经典的开心果口味,远远望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昂首阔步中一展胳膊搂住身旁母亲的肩。她爱怜地仰起头,长裙飘在傍晚的风里。即便隔着一条街你也能读懂,她眼里写不尽的自豪与期待。你安静地眺望,这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夜晚。
就着家长满溢的热情,学校在正式的毕业典礼前安排了许多活动。这一天下午,耶鲁的校长和教导主任举办招待会。两位西装革履的大人物并排站好,在艳阳高照下与毕业生及家人一张张合影,微笑的弧度中透出耐心,额头的汗珠里滴着敬业。前一天下午,耶鲁的吉祥物也有过一场合影活动。那是一只名为Handsome Dan的斗牛犬,名号传了一百多年到今天。据说第一世曾在橄榄球赛上对着“哈佛红”狂吠,如今的第十九世也不改颜色,总是一副睥睨万物、桀骜不驯的样子。无论看哪张照片,他一定梗起脖子,臭着一张脸,被学生团团簇拥。这待遇,大概比英女王的柯基犬有过之而无不及。
等到毕业典礼真的开始,校长大概会在致辞里鼓舞大家,“耶鲁学生是一群要改变世界的人”。来到这古老的校园度过四年青春,也许这是我们最初的信仰。只是,台下的毕业生早已铺就未来的坦途,大多不是金融咨询,就是科技大厂。据说大一的学子总对“向钱看”的职业选择不屑低头,但升入要为稻粱谋的高年级后,又会转身挤破脑袋渴望“上岸”。也许改变世界早就是遗留在上一个时代的梦想,也许做好自己、活在当下已是顺其自然改变世界的方式。也许世界从未等待着被谁改变,浩浩汤汤的大潮裹挟着人群奔涌而去。也许宿命的旋钮突然转起,只因某一丝心神在校长的恳切教导下微微一动,于是毅然离开舒适与优渥,投入艰苦卓绝的征程中来。也许时间本不曾沿一条直线向前流动,而是在铺张开来混乱的一池水里挣扎。矛盾与追问在这里汇聚、杂糅、交错,然后归于平静。一届又一届学生毕业,我们静静远观。戴着学士帽的人群黑压压坐在青绿的草坪上,那是时代的剪影。
两场盛大的毕业典礼后,两年的时光像是被偷去了一样。我怀疑人为什么执着于仪式,想起一场场生日、婚礼、葬礼,感叹人是如此善于,又如此需要赋予意义。生命是一个过程,假如不浓墨重彩地点上一笔,时间便在一念之间呼啸而去了。我们手里仅剩下抻得无限长的回忆,滑溜溜的,抓也不住。也许我们需要亲朋好友见证这个时刻,在肆意挥洒的阳光里走上讲台,由校长轻轻地拨一下学士帽上的穗,再抬头时笑得张扬又谦卑。也许这算是毕业典礼的某种意义:一颗年轻的心在喜乐祥和中对未来释然,于生命的又一节点沐浴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