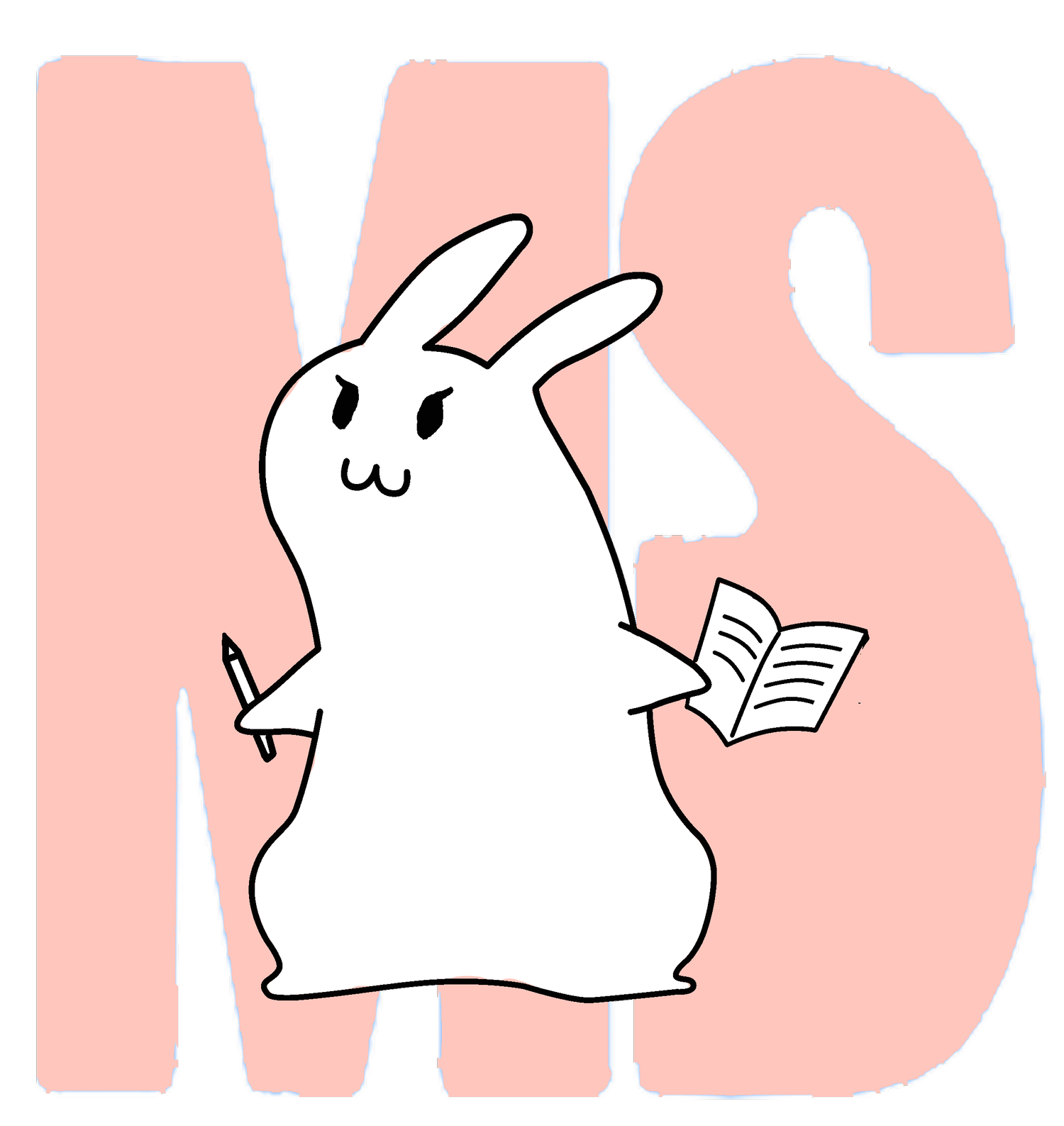在纽约,奇怪地活着
纽约?太奇怪一个地方。
其一,很容易感冒,不怪秋裤,就怪地铁。等车的通道像风箱,烘人烘得熟熟透透的。轿厢里冷得要被凝固住一样,使人不再自我认同为沙丁鱼罐头,而成为超市甩卖不完的冰冻带鱼。一冷一热,交替不断,成功着凉。
上课的时候,擤鼻涕到大脑缺氧;和教授聊天,一抽一抽很有节奏。也不能说尴尬,或笨拙,只是变了一样姿态,以一种脸先着地的优雅,太迷路而降临地球。神思恍惚间,心头响起教导主任的声音:一天天的,活在梦里。
其二,金钱观扭曲,穷到深处自然富。月租两千多的公寓稀松平常,咖啡八块钱一杯实在嫌贵。假如不幸地乳糖不耐,又要多加一刀喝燕麦奶。什么植物啦这么金贵,比牛多值出七块人民币来?
后来学乖了,不折算汇率了,才又稳住内心世界的宁静。静得像尼斯湖的水面,盖住内里的幽暗深沉,恐怕随时冒头一只恐龙状的黑影。又或者是鄱阳湖好了,驻足岸边眺望,如画如歌,一碧万顷,直到晚霞惊起时光的褶皱,血浪滔天的战场横现眼前。
活在资本主义的直辖市,做一个不赚钱的穷学生,心如此湖。波光粼粼只是表象——意识到自己每天花五十块人民币坐地铁的时候,我正走进纽约连绵的细雨里,没带伞。秋日的雾霭迷蒙,自有一番朱元璋大战水怪的悲壮。
其三,新奇又陌生,走到哪都像旅游。虽然林立的高楼最典型,但其实纽约的臂展很长,胸膛宽阔。在半小时地铁外的布鲁克林,联排的小房子串起涂鸦的街道。总有人笑言他是艺术家,总有人约你来喝杯酒吧。还有市政府帮建的住宅楼,似在深棕色一只大纸箱上,捅出规规整整的方块小洞。深蓝的暮色里,稀疏的住户出入,无声无息,行走飘忽如在游戏建模里。
哐当一小时外的皇后区,法拉盛像一座平移过海的县城。热热闹闹的灯火亮着,火锅店热腾腾地涮着。菜市场总在喧嚣,按摩店门口的女人还在等。不过硕大的中文花字招牌下,会印上小小工整的一排英文,给隔壁区amigo——西班牙语的“朋友”,当地人如此称呼西裔人群——行个方便罢了。
当然,还有更多细碎的参考。周末晚间的韩国城,像拥挤版的三里屯。河边的哈德逊广场,是不见了大裤衩的国贸。雨中尖顶的教堂使人想起伦敦,哥大新古典的图书馆又扯上点巴黎。
纽约的这里那里,尽可以做全世界的集合体。但又常常不是,常常在鱼龙混杂时泾渭分明,在慌张无措中怡然自得——好比幸运得拥有一切选择的人,常常在纯粹的实质上一无所有。
教授说,学完走吧,世界很大,纽约太贵,不值当的。他明明年届五十,身穿西装,却脱不去一身少年气,只是变得幽微,惯会隐去。看向他深陷的眼睛里,会染上暖黄灯光下书本的昏沉。
“可你不是还在这里,”我反问。“因为我教书啊,被困住了,”他答得理所当然,仿佛在谈万有引力。十几年前,他回纽约,创立风靡文化圈的杂志《N+1》,因此得到哥大新闻系的教职。The rest is history:上课,他给全班讲自己在俄乌战争中的报道;下课,同学在网上读他去年差点离婚的八卦。
从教授一句爱恨交缠的忠告里,我好像瞥见了纽约真正的模样。布鲁克林的艺术家会长大,会成功,会过上看似稳定的生活,却又忍不住暗地里波涛汹涌。人和钱总要一直不停地发生关系,要轻蔑,要渴望,再将过去时间打成的结一缕缕织进书里,卖不卖的出去只当是下一场听天由命。
纽约是这样的。走在路上,迷乱如王家卫;坐在风里,荒凉似贾樟柯。文艺青年来了又走,金融才俊引吭高歌。没有什么不是病着的,不是在冷热交替里茫然着、眩晕着的。在贫瘠的沙漠里,才能长出甜美多汁的水果;在丰饶的海洋里,才游动着奇形怪状的生物。
奇怪是这样的,很奇怪,但因为在一座这样的城里,奇怪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