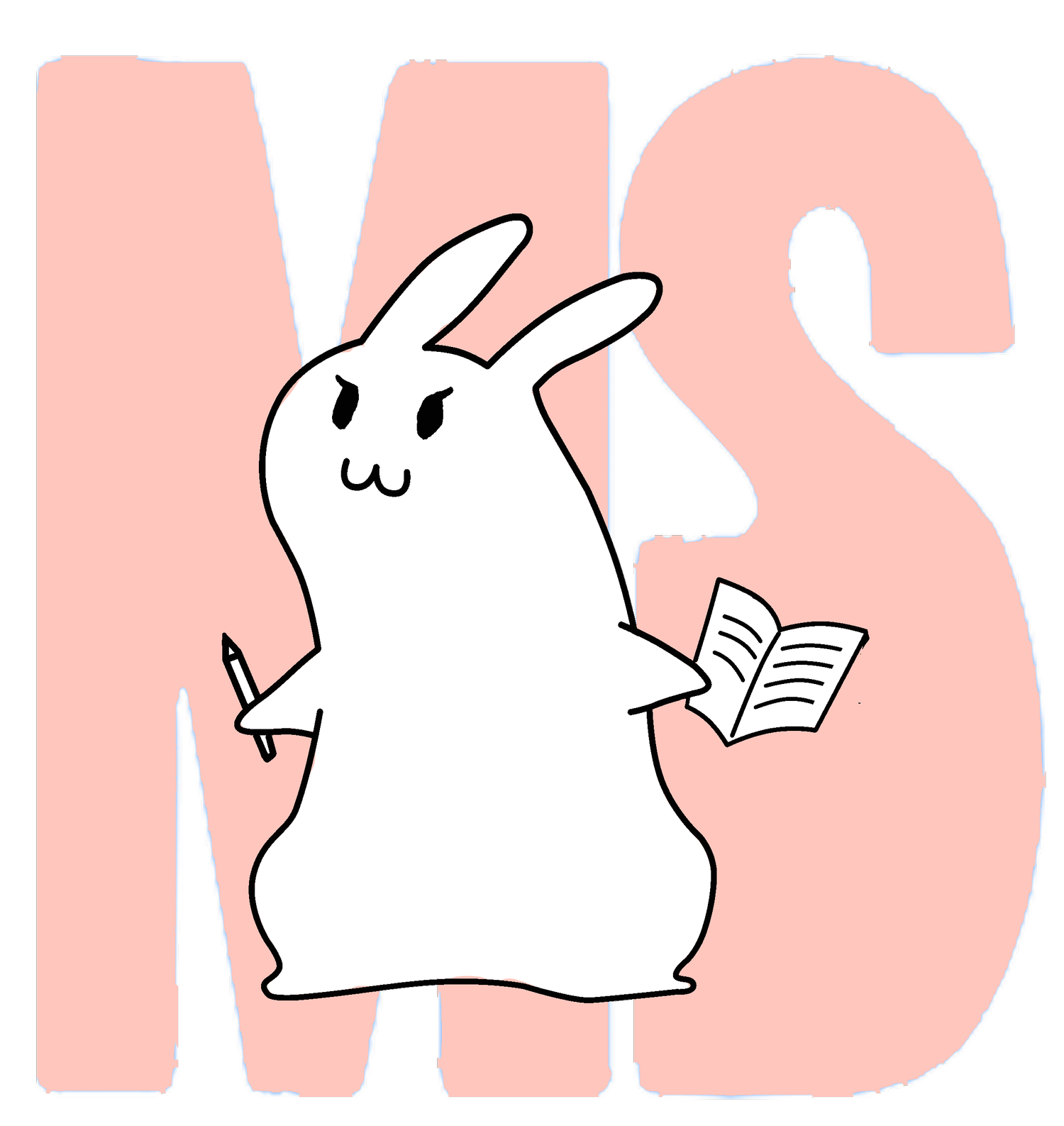纽约第一关
进美国第一道门,是JFK机场的海关。
长长一排四面围合的办公桌前,弯弯曲曲折起两条队伍:citizen(公民)和visitor(访客)。护照不同,千姿百态起来却不分伯仲:肤色体态各异,贫富阶级俱有,从全套LV的旅行包,到灿如春光的纱丽,从热热闹闹的大家庭,到孑然一身的旅行者,各自闷于长途旅行的疲惫,不堪百无聊赖的等待。
高挂于天花板的电视机上,循环播放着加入美国籍的广告:一群人露出大白牙挥舞星条旗,甚至戴上西部牛仔的宽檐帽,站在蓝天笼罩的高山峡谷前,头顶上闪现白色大字 choose opportunity(选择机会)。电视里还有人维持秩序,一颦一笑像是AI版的芭比娃娃,现实中也有人引导排队,蛤蟆样的褶皱从嘴角重重耷拉下去。
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中年男士,身着熨贴的墨蓝风衣,剃了贝佐斯一样的光头,也挺着同他一般厚大的鼻子,两片薄薄的嘴唇几乎没进皮肤里,一笑便消失了,活像布隆伯格的竞选广告。不远处站了几位青年学子,一人手里拎好一只文件袋,一沓护照资料一应俱全。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也曾端起这般严谨的态度,远胜今天一通乱揣,两兜里鼓鼓囊囊的。队尾迎来一个家庭,女儿坐在父亲的鞋面上,臂窝里伸出一只毛绒大鹅的脖子来,和顺地弯弯垂下,长长的喙吻上地板,随着脚步一啄一啄地往前蹭。母亲戴了头巾,圆滚滚的双颊泛起粉红,好像米勒画上田间收获的妇女。
空中浮着香蕉熟透了的气息,由低矮的天花板压进人群里,弥散在灰白的墙壁和柱子间。跳过屏风一样的一排办公桌,横过一条细长的走廊,若向右拐,便能顺利进入开阔的行李大厅,若往左行,则意味着要被领入“小黑屋”等待。疫情期间,为了回校上学,我们一飞机北京来的留学生,几乎都被提溜进屋关过一圈。不同于想象中谍战片的审讯室,听候发落的房间很大、很亮,只是没有窗户,灯光泛着冷冷的白。
海关的办公桌笼在透明围墙里,竖在不高的台子上,几排金属椅子坐满了暂失护照、两手空空的人——干坐,不让玩手机。等叫名字还不够,得竖起耳朵努力找,毕竟美国人很难发好中文的音。无聊,又无助。有时候一叠护照拿出来发,领证走人,有时候叫到近前讲两句话,敲章通过,还有可能套娃般再次左拐,送进一对一的小办公室,细细盘问。三种情况都会发生,护照排序也很随意。海关的权力好比命运,凭心情往人间掷骰子。
这一回,我边排队边探头探脑:还好,“小黑屋”通道看着很空。快轮到时,“访客”的一条长队被分成平行的几支小队。站在我旁边的大叔,胡子拉碴,胸肌往上快要顶到下巴,比《封神》的费翔还要凸出。一家子穆斯林正接受询问,年迈的阿姨几乎没在黑色头巾里,在海关官员的指导下录入指纹,脚边放着花花绿绿一只大蛇皮袋,在通关后被她的儿子一提就走。
下一位,是排我前面的光头得体男。他开了两个不痛不痒的玩笑,迷人的蓝色眼睛落在玻璃上,却被目的地拒收——电脑前身穿制服的年轻女士,头也不抬,翻着护照,向他要来美的原因、在美的行程、暂住的地点。“我常来,上次仅仅是五周前。”他乖乖描述一遍行程,又报出一所高档酒店的名字,一副自来熟的口气,结果碰上了软钉子。“我问的是地址,”海关强忍着不耐烦道。他只好掏出手机,照着将几街几号全念一遍。然后,随着“咔嚓”一声响,印章在签证页落定,他被放行。
我们分明知晓,每天敲章的海关工作人员,不过是公权力的细枝末梢。他们在围栏里坐困愁城,恨不得不要板着脸,早点下班伸个懒腰。但奇怪的是,只用短短几分钟,他们似乎能磨平财富、阶层的巨大鸿沟——管你是泼天富贵还是勉强温饱,只要一下飞机,必经海关大厅,通通给我恪守规矩、老实交代。当然,屏息凝神的时刻过后,上了封条的空气瞬间解开,各人走各人的命运之路去了。
等轮到我,掏出护照好好送进去,聊上两句,眼瞧着又顺利递出来,点头道谢,快步离去,长舒一口气。这一过海关,一取行李,一坐地铁,算是真来了纽约。深一脚,浅一脚,我踏足这光怪陆离的世界,不由自主随着茫茫人海漂远了。